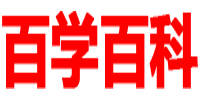(战国策魏策古诗文网)战国策魏策
今天百学百科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战国策魏策,以下关于战国策魏策古诗文网的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学习。
《战国策 魏策》翻译
最佳答案翻译:
魏王准备攻打邯郸,季梁听到这件事,半路上就返回来,来不及管衣着不整,顾不得洗头上的尘土,就忙着去谒见魏王,说:“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路上遇见一个人,正在向北面赶他的车,他告诉我说:‘我想到楚国去。’
我说:‘您既然要到楚国去,怎么往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他又说:‘我的车夫善于赶车。’
我最后说:‘这几样越好,反而会使您离楚国越远!’如今大王的每一个行动都想建立霸业,每一个行动都想在天下取得威信;然而依仗魏国的强大,军队的精良,而去攻打邯郸,以使土地扩展,名分尊贵,大王这样的行动越多,那么距离大王的事业无疑是越来越远。这不是和那位想到楚国去的人一样了吗?
原文:
魏王(魏惠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
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於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此文出自战国时期·刘向《战国策·魏策》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
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
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编订,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
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史料。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司马迁在《苏秦传》后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作者简介:
刘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世居汉代楚国彭城,仕于京师长安,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徐州),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刘歆之父。
其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任宗正,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刘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
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战国策•魏策>>全文及解释
最佳答案《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策一(知伯索地于魏桓子)
【提要】“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魏桓子采用“欲擒故纵”的谋略,消灭了骄狂膨胀的知伯。这个事典倒应了西方的那句谚语:“上帝要叫一个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
【原文】知伯索地于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邻国必恐;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伯必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氏之命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君不如与之,以骄知伯。君何释以天下图知氏,而独以吾国为知氏质乎”君曰:“善。”乃与之万家之邑一。知伯大说,因索蔡、皋梁于赵,赵弗与,因围晋阳。韩、魏反于外,赵氏应之于内,知氏遂亡。
【译文】知伯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不给。任章问他道:“怎么不给他呢”桓子说:“无缘无故来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没有缘由就索取土地,邻国一定害怕;胃口太大又不知满足,诸侯一定都害怕。假使你把土地给了他,知伯必定越发骄横。一骄横就会轻敌,邻国害怕就自然会相互团结。用相互团结的军队来防御对付轻敌的国家。知伯肯定活不长了!《周书》上说:’想要打败他,一定先要帮他一把;想要夺取他,一定先要给他一点。’所以您不如把土地给他,以便使知伯越来越骄横。您怎么能放弃和天下诸侯共同图谋知伯的机会,却偏偏让我国成为知伯的攻击对象呢”魏桓子:“好吧。”于是就把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城邑给了知伯。知伯很高兴,于是就又向赵国索取蔡、皋狼等地,赵国不答应,知伯就围攻晋阳。这时韩魏从国外反击,赵氏从国内接应,知伯于是是很快就灭亡了。后来韩赵之间又发生争执。韩国去向魏国借兵说:“希望能借给我军队来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和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遵命。”不久,赵国又向魏国借兵去攻打韩国,魏文侯说:“我和韩国是兄弟之邦,不敢遵命。”两国都没借到兵,就生气地返回本国。过后才知道魏文侯在中间替他们讲和,因此,都来朝拜魏国。
【评析】谋士的高明就在于能够反常思维,而且看问题看得长远。一般人面对知伯的无理要求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但是谋略家们就具有不同于常人的心态和思维,用表面的、暂时的曲意逢迎换来最终的胜利和报仇雪恨。这种迂回曲折的思维方式,是谋略的一大特色。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也会遇到众多狂妄自大的人,对待这类人大可不必直接顶撞,我们完全可以在忍耐等待中寻求众人的支持,因为狂妄自大,必然招致众怨,引起众怒。多行不义必自毙,看你横行到几时。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策一(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
【提要】乐羊食子,这无疑是古代发生的人间的悲剧。但是同是此事,却引来截然不同的看法。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是谋略学的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此篇中得以表现。
【原文】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睹师赞曰:“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赞对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乐羊既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译文】乐羊作为魏国的将领攻打中山国。当时他的儿子就在中山国内,中山国国君把他的儿子煮成人肉羹送给他。乐羊就坐在军帐内端着肉羹喝了起来,一杯全喝完了。魏文侯对睹师赞说:“乐羊为了我的国家,竟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睹师赞却说:“连儿子的肉都吃了,还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乐羊攻占中山国之后,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的战功,却怀疑起他的心地来。
【评析】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吗乐羊的手段大大地违背了目的,丧失了人道,竟让人怀疑起他的人性来。“文革”期间为了“革命”很多人连亲人都陷害、残害,人伦道德丝毫不顾,要这样的“革命”干什么呢?故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打着革命、国家、人道等漂亮旗号而实际上心地残忍、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他们为一些骗人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就是他们的目的实现了,他们在人格上的失败也是注定的。
人们一般认为,政治家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际上,手段还是要进行选择的。首先,手段取决于目的,这个目的一定是要正确的,有关国家大义的;其次,要看这个手段能否达成目的,如果手段本身的使用违背了目的,使用手段造成的负效大于目的应产生的效益,那么这个手段是不应该采取的。
符合上述二点要求的高明手段很多,如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造成数十万人丧生,但却迫使日本投降。如果采取进攻日本本土迫使其投降的手段,估计死亡人数倍于广岛、长崎居民。在这里,作为手段的投放原子弹虽然造成不少负效,但却避免了其他手段造成的更大负效,赢得了政治目的的实现。在上述例子中,1美军是为了国家大义。2他们的手段都达到了目的,手段负效明显小于目的之正效。
在错误的决策中,手段产生的负效往往大于目的之效益。如有人认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为了赶走李自成,复兴明朝。清兵入关后虽达成了吴的一部分目的,但其的负效——中国沦落在满清手中却使吴三桂落下千古骂名。吴的决策失误在于手段背离了目的。
乐羊之引人怀疑,在于他使用的手段过于残酷,大大超过甚至背离了对国家表达忠心这个目的。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提要】地形、地缘在军事、政治上具有很高的位置,地缘政治学的兴盛就昭示出这个道理。然而魏国大臣吴起打破了对地形的迷信,说明就修明政务和地形两者而言,修明政务更重要。
【原文】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钟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缴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
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
【译文】魏武侯和大臣们乘船在西河上游玩,魏武侯赞叹道:“河山这样的险峻,边防难道不是很坚固吗!”大臣王钟在旁边陪坐,说:“这就是晋国强大的原因。如果再修明政治,那么我们魏国称霸天下的条件就具备了。”吴起回答说:“我们君主的话,是危国言论;可是你又来附和,这就更加危险了。”
武侯很气愤地说:“你这话是什么道理”吴起回答说:“河山的险是不能依靠的,霸业从不在河山险要处产生。过去三苗居住的地方,左有彭蠡湖,右有洞庭湖,岐山居北面,衡山处南面。虽然有这些天险依仗,可是政事治理不好,结果大禹赶走了他们。夏桀的国家,左面是天门山的北麓,右边是天溪山的南边,庐山和峄山在二山北部,伊水、洛水流经它的南面。有这样的天险,但是没有治理好国政,结果被商汤攻破了。殷纣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漳水和滏水,前面对着黄河,后面靠着山。虽有这样的天险,然而国家治理不好,遭到周武王的讨伐。再说您曾经亲自率领我们占领、攻陷了多少城邑,那些城的墙不是不高,人不是不多,然而能够攻破它们,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政治腐败的缘故吗由此看来,靠着地形险峻,怎么能成就霸业呢”武侯说:“好啊。我今天终于听到明哲的政论了!西河的政务,就全托付给您了。”
【评析】古往今来的社会兴衰,关键因素是国家的政务是否清明、制度是否进步。至于地形、自然灾害之类的原因只是枝节问题。同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就是两个不同的面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家之间自然资源相差不大,但强弱兴衰各有不同,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制度不同。所以制度的进步才是国家兴盛的关键。
吴起非常善于说服君王,首先他以惊人之语抓住了听众的心,他居然说君主的话是危国之言,这确实是很好的开场白。然后他列举三苗、夏桀、殷纣虽有地理天险但由于国家不能治理而亡国的先例,最后现身说法,从听众的亲身经历再次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整个论证具有事实和逻辑的强大力量,听后不能不折服于吴起的雄辩与高见。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
【提要】苏秦的合纵战略必须在除秦之外的每个国家都要实施,所以苏秦不遗余力,到各个国家游说。他的合纵游说的主旨和形式大同小异,但每篇游说对我们演练揣摩论辩技能都大有裨益。
【原文】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繴;东有淮、颖、沂、黄、煮枣、海盐、无繵;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然横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愧之。
臣闻越王勾践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斩纣于牧之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振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千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勾践、武王远矣。今乃于辟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质,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使臣献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译文】苏秦为了赵国合纵游说魏襄王道:“大王的国土,南边有鸿沟、陈地、汝南,还有许地、鄢地、昆阳、召陵、舞阳、新;东边有淮水、颍水、沂水、外黄、煮枣、海盐、无;西有长城边界;北有河外、卷地、衍地、酸枣,土地纵横千里。地方名义上虽然狭小,但房屋田舍十分密集,甚至没有放牧牛马的地方。人民众多,车马成群,日夜奔驰,络绎不绝,其声势和三军士兵相比没有什么区别。我私下里估计,大王的国力不亚于楚国。然而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却劝说大王结交像虎狼一样强暴的秦国,若国家因此遭受祸患,他们又不肯为您分忧。他们依仗强秦的势力,在国内胁迫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再说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君主,如今竟有意投向西方服事秦国,自称是秦国东方的属国,建筑秦帝行宫,接受秦的封赏,春秋两季给它进贡助祭,我心里替大王惭愧。
听说越王勾践靠三千残兵败将,在于隧擒获了夫差;周武王也仅有三千士兵,三百辆战车,在牧野杀死了商纣王。难道是他们土兵多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能振奋自己的雄威啊!如今我听说大王的兵力,常备军二十万,青布裹头的士兵二十万,精兵二十万,勤杂部队十万,还有六百辆战车,五千匹战马。这肯定远远超过越王勾践和武王的力量!如今您却迫于谗臣的邪说,想要臣服于秦国。事奉秦国一定得割让土地送上人质,因此军队还没用上而国家的元气已经亏损了。群臣之中凡是主张事奉秦国的人,都是奸臣,绝不是忠臣。作为臣子却割让君主的土地与外国勾结;窃取一时的功名和好处,却不顾及后患;损害国家的利益,去满足个人的私利与欲望;在国外仰仗强秦威势,在国内胁迫自己的君主割让土地,对于卑劣行为,希望大王慎重考虑。
《周书》上说:‘微弱时如不及早斩断,等到长大了就没办法;幼小时如不及早铲除,将来长大了就得用斧头砍。’事先要当机立断,否则事后必有大祸,到那时不知怎么办。如果大王真能听从我的意见,六国合纵相亲,齐心合力,就一定不会遭受强秦的侵犯。所以敝国赵王派我来进献愚计,呈上盟约,听凭大王诏令。”魏王说:“我没有才能,以前从未听过这样高明的指教。现在您以赵王的诏令来教导我,我愿意率领全国民众听从您的安排。”
【评析】苏秦的合纵游说,最大特点就在于鼓舞各国的决不屈服的斗志。当时各国摄于秦国的淫威,意志和精神都快要崩溃。鼓舞他人,首先要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重估自己的价值,重新树立独立自主、决不俯首称臣的信心。在说明魏国实力的同时,苏秦又列举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众多事例,还针锋相对、斥责那些连横事秦者道德上的卑污。最后又鼓励魏王当机立断,走向联合抗秦的道路。一番慷慨陈词,一气呵成,让人精神上受到鼓舞,道理上认清了形势,确实树立了抗暴的信心。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
【提要】张仪与苏秦面对同一个游说对象,互相攻击,指斥对方人格的卑污,渲染各自主张的好处。这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另一个刀光剑影的战场,一切兵戈战争其实早已在论辩中决出了胜负。
【原文】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繶,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合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夫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以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枣,劫卫取晋阳,则赵不南;赵不南则魏不北,魏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求无危,不可得也。秦挟韩而攻魏,韩劫于秦,不敢不听。秦、韩为一国,魏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言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魏之兵南面而伐,胜楚必矣。夫亏楚而益魏,攻楚而适秦,内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甲出而东,虽欲事秦而不可得也。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寡可信,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繷腕、繸目、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览其辞,牵其说,恶得无眩哉臣闻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计失之。请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
【译文】张仪为秦国连横之事,去游说魏襄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一千里,士兵不超过三十万人。四周地势平坦,与四方诸侯交通便利,犹如车轮辐条都集聚在车轴上一般,更没有高山深川的阻隔。从郑国到魏国,不过百来里;从陈国到魏国,也只有二百余里。人奔马跑,等不到疲倦就到了魏国。南边与楚国接壤,西边是韩国,北边是赵国,东边与齐国相邻,魏国士兵要守卫四方边界。守境的小亭和屏障接连排列。运粮的河道和储米的粮仓,不少于十万。魏国的地势,原本就是适合作战的地方。如果魏国向南亲近楚国而不亲近齐国,那齐国就会进攻你们的东面;向东亲附齐国而不亲附赵国,那赵国就会由北面来进攻你们;不和韩国联合,那么韩国就会攻打你们西面;不和楚国亲善,那南面就会危险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地理位置。
再说诸侯组织合纵阵线,说是为了使社稷安定,君主尊贵,兵力强大,名声显赫。现在合纵的国家想要联合诸侯,结为兄弟,在洹水之滨宰杀白马,歃血为盟,以示坚守信约。然而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尚且还有争夺钱财的。而您却想依靠欺诈虚伪、反复无常的苏秦所残留的计策,这明显不可能成功。如果大王不臣服于秦国,秦国将发兵进攻河外,占领卷、衍、南燕、酸枣等地,胁迫卫国夺取晋阳,那么赵国就不能南下支援魏国;赵国不能南下,那么魏国也就不能北上联合赵国;魏国不能联络赵国,那么合纵的通道就断绝了。合纵的通道一断,那么大王的国家再想不危险就不可能了。再有,秦国若是挟制韩国来攻打魏国,韩国迫于秦国的压力,一定不敢不听从。秦韩结为一体,那魏国灭亡之期就不远了,这就是我为大王担心的原因。我替大王考虑,不如归顺秦国,归顺了秦国,那么楚韩必定不敢轻举妄动;没了楚韩的侵扰,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国家也一定不会有忧患了。
再说,秦国想要削弱的莫过于楚国,而能抑制楚国的又莫不过魏国。楚国虽然有富足强大的名声,但实际上空虚得很;它的士兵虽然多,但大部分容易逃跑败退,不敢打硬仗;如果出动魏国军队向南讨伐,必定能战胜楚国。这样看来,让楚国吃亏而魏国得到好处,攻打楚国取悦秦国,把灾祸转嫁给别人,安定国家,这可是件大好事啊。大王如果不听我的意见,秦兵出动,即使想归顺也不可能了。而且主张合纵的人大都夸大其辞、不可信赖,他们游说一个君主,出来就乘坐那个君主赏赐给他的车子,联合一个诸侯成功返回故国,他就有了封侯的资本。所以天下游说之士,没有不每天都捏着手腕,瞪着眼睛,咬牙切齿地高谈阔论合纵的好处,以博得君王的欢心。君王们接受他们的巧辩,被他们的空话牵动,怎能不头昏目眩呢我听说羽毛多了也可以压沉船只,轻的东西装多了也可以压断车轴,众口一词足以熔化金属,所以请大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魏王说:“我太愚蠢,以前的策略错了。我愿意做秦国东方的藩臣,给秦王修建行宫,接受秦国的封赏,春秋两季贡献祭品,并献上河外的土地。”
【评析】这次苏秦与张仪的论辩,看来还是以张仪获胜而告终。张仪的连横游说向来以暴力威胁为后盾,大肆渲染秦国武力侵略的严重后果,让弱国的国君胆战心惊。如果说苏秦在进行鼓舞斗志的工作的话,那么张仪就在进瓦解斗志的工作。
同是一个魏国,在苏秦看来既有地缘优势,又实力雄厚、足以与秦国抗衡;在张仪口中却变得势单力薄,地理上也处于四分五裂的位置,惟有侍奉秦国别无出路。语言对事实的改变、颠倒作用如此巨大,以致魏王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同是合纵,在苏秦看来必能形成抗衡强秦的联盟和战略,在张仪看来由于利益不同、人心不合,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历史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张仪的洞见,但无论胜败,苏秦和张仪的雄辩都值得千古传诵、研读。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策一(张仪以秦相魏)
【提要】机警过人的张仪也经常有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次幸得富有谋略、能言善变的雍沮的举手之劳,才化解了危机。
【原文】张子仪以秦相魏,齐、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谓张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则国家安,而百姓无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计过也。齐、楚攻魏,公必危矣。”张子曰:“然则奈何”雍沮曰:“请令齐、楚解攻。”
雍沮谓齐、楚之君曰:“王亦闻张仪之约秦王乎?曰:‘王若相仪于魏,齐、楚恶仪,必攻魏。魏战而胜,是齐、楚之兵折,而仪固得魏矣;若不胜魏,魏必多秦以持其国,必割地以赂王。若欲复攻,其敝不足以应秦。’此仪之所以与秦王阴相结也。今仪相魏而攻之,是使仪之计当与秦也,非所以穷仪之道也。”齐、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于魏。
【译文】张仪凭借秦国的势力在魏国任相国,齐、楚两国很气愤,就想攻打魏国。雍沮对张仪说:“魏国之所以让您做相国,是以为您做相国国家可以安宁。如今您为相国,魏国却遭受兵祸,这说明魏国的想法错了。倘若齐楚进攻魏国,您的处境就危险了。”张仪说:“既然这样,那该怎么办呢”雍沮说:“请让我去劝说齐楚两国放弃攻魏。”
于是雍沮去对齐楚的君主说:“大王可曾听说张仪和秦惠王订密约的事吗张仪说:‘大王如果能让我到魏国做国相,齐楚恨我,必定攻打魏国。若是魏国战胜了,齐、楚两国的兵力就会受损失,我就顺理成章出任魏相;若是魏国战败,魏国一定投靠秦国来保全自己的国家,必然割地给大王。齐、楚两国如果再想进攻魏国,它们已十分疲惫,怎么能与邦国周旋呢。’这就是张仪和秦王暗中勾结的原因。现在你们去攻打魏国,会促使张仪的计谋实现,而不是困厄张仪的办法。”齐楚两国的君主都说:“对。”于是立即不攻魏国。
【评析】雍沮解救张仪,在于充分利用了齐、楚两国对张仪的仇恨,让敌方误以为行使计谋会陷进圈套,告知敌方这样的计划非但达成不了目的,反而会帮倒忙,于是敌方就会放弃计划,从而挫败了敌方的原来有害于我方的谋划。这就是称为“将计就计”的谋略。谋略家们想得广、看得远,料事如神,经常指出各种事情的结果,你如果能经常在事情之初就判断它的结果的多种可能性,那么你的预见能力和说服能力就会大大加强。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策一(公孙衍为魏将)
【提要】再也没有比类比更能说明问题的论辩方法了。我们说话时一定要多用它。
【原文】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绎不善。季子为衍谓梁王曰:“王独不见夫服牛骖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也。牛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国必伤矣!愿王察之。”
【译文】公孙衍做魏国大将时,和魏相国田不睦。季子替公孙衍对魏王说:“大王难道不知道用牛驾辕、用千里马拉套连一百步也不可能赶到的事吗?现在大王认为公孙衍是可以领兵的将领,因此任用他;然而您又听信相国的主意,这明显是用牛驾辕、用千里马拉套的做法。即使牛马都累死,也不能把国事做好,国家的利益势必要受到损伤!希望大王明察。”
【评析】类比方法形象、生动、易于理解,但进行类比的两事物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讲,从“用牛驾辕、用千里马拉套不会走动”是推不出国家有别扭的两重臣不能共事的结论的。但是,人们的类比又告知人们两者的相似性、可类比性。其实惯于形象思维的我们是最易接受类比的。
《战国策》卷二十三 魏策二
以“吃硬寨打死仗”著称的曾国藩不喜欢说“大言”的人,认为夸夸其谈、浮夸虚假、于事无补。然而就游说来说有时就不能不说大话。
《战国策》卷二十三 魏策二(犀首田盼欲得齐魏之兵)
【原文】犀首、田盼欲得齐、魏之兵以伐赵,梁君与田侯不欲。犀首曰:“请国出五万人,不过五月而赵破。”田盼曰:“夫轻用其兵者,其国易危;易用其计者,其身易穷。公今言破赵大易,恐有后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难以惧之,是赵不伐,而二士之谋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难构而兵结,田侯、梁君见其危,又安敢释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劝两君听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齐、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战败也,悉起兵从之,大败赵氏。
【译文】犀首和田盼想率领齐、魏两国的军队去攻打赵国,魏王和齐王不同意。犀首说:“请两国各出五万兵力,不超过五个月就能攻下赵国。”田盼却说:“轻易动用军队,这样的国家容易出现危险;轻易使用计谋,这样的人也容易陷入困境。您现在对攻下赵国说得也太容易了,恐有后患。”犀首说:“您太糊涂了。那二位君主,本来就已经不想出兵。今天您又说出困难来吓唬他们,这样不但赵国不能攻打,而且我们两人的图谋也要破产了。如果您干脆就说很容易,那么两国君王的顾虑就消除了。等到双方交战,短兵相接,齐王和魏王看到形势危险,又怎么敢放着军队不给我们用呢”田盼说:“对。”于是就合力劝说两国君主听从犀首的意见。犀首、田盼于是得到齐、魏两军的指挥权。军队还没有开出国境,魏王和齐王担心他们到了赵国要吃败仗,就调集全部军队紧跟而来,结果彻底击败了赵国。
【评析】犀首敢说大话在于他掌握对方的心理,如果是平实、客观的论说,怎么能激发起对方的兴趣、打动对事不明、尚在犹豫不决中的对方呢?所以论辩时有时就要加重力度、极力渲染,这样才能收到谋求的效果。这样做也不是不诚实,而是能够进一步施展计谋,最后达成自己所许诺的事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等事情成了这种状况的时候,对方与你会一致努力成全事功的。
另附战国策全文及译文如附件,可下载观看,都有
满意请
战国策·魏策三
最佳答案战国策全文 魏策三○秦赵约而伐魏
秦、赵约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忧也,臣请发张倚使谓赵王曰:
‘夫邺,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邺事大王。’”赵王喜,
召相国而命之曰:“魏王邺事寡人,使寡人绝秦。”相国曰:“收秦攻魏,
利不过邺。今不用兵而得邺,请许魏。”张倚因谓赵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
在邺矣。大王且何以报魏?”赵王因令闭关绝秦,秦、赵大恶。芒卯应赵使曰:
“敝邑所以事大王者,为完邺也。今郊邺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赵王恐
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
○芒卯谓秦王
芒卯谓秦王曰:“王之士未有为之中者也。臣闻明王不胥中而行。王之所欲
于魏者,长羊、王福、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为魏之司徒,则臣能使魏献之。”
秦王曰:“善。”因任之以为魏司徒。
谓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于魏者,长羊、王屋、洛林之地也。
王献之秦,则上地无忧患,因下东击额齐,攘地必远矣。”魏王曰:“善。”
因献之秦。地入数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谓芒卯曰:“地已入数月而秦兵不下,
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虽然,臣死则契折于秦,王无以责秦。王因赦其
罪,臣为王责约于秦。”乃之秦,谓秦王曰:“魏之所以献长羊、王屋、洛林之
地者,有意欲与下大王之兵东击齐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则死人也。
虽然,后山东之士无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惧然曰:“国有事,为澹下兵也,今
以兵从。”后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将秦、魏之兵,以东击齐,启地二十二县。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须贾为魏谓穰侯曰:“臣闻魏氏大臣父兄皆
谓魏王曰:‘初时惠王伐赵,战胜乎三梁,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
复归。齐人攻燕,杀子之,破故国,燕不割,而燕国复归。燕、赵之所以国全兵
劲而地不并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数割,而随以亡。
臣以为燕、赵可法,而宋、中山可无为也。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尽晋
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
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听也。今王循楚、赵而讲,楚、
赵怒而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则国救亡不可得也已,
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必割而有质;不然必欺。’是臣之所闻于魏也,愿
君之以是虑事也。
“《周书》曰:‘维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而割八县,
此非兵力之精,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
天幸自为常也。知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
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夫轻信楚、赵之
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
未尝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罢,阴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愿之及楚、赵之兵未任于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
为和,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于魏之先己讲也,必争事秦。从是以散,
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尝割晋国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绛、安邑,
又为阴启两,机尽故宋,卫效尤惮。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
不成?臣愿君之熟计而无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罢梁围。
○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
秦败魏于华,魏王且入朝于秦。周谓王曰:“宋人有学者,三年反而名其
母。其母曰:‘子学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贤者无过尧、舜,
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贤不过尧、舜,母大不过天地,是
以名利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学者,将尽行之乎?愿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
之于学也,将有所不行乎?愿子之且以名母为后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
入朝者乎?愿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为后。”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
许绾为我祝曰:‘入而不出,请殉寡人以头。’”周对曰:“若臣之贱也,今
人有谓臣曰:‘入不测之渊而必出,不出,一鼠首为女殉者,臣必不为也。
今秦不可知之国也,犹不测之渊也。而许绾之首,犹鼠首也。内王于不可知之秦,
而殉王以鼠首,臣窃为王不取也。且无梁孰与无河内急?”王曰:“梁急。”
“无梁孰与无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内其下也。
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
王尚未听也。支期曰:“王视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
楚、魏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谓支期曰:“吾始已诺于应侯矣,今不
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忧也,臣使长信侯请无内王,王待臣也。”支期
说于长信侯曰:“王命召相国。”长信侯曰:“王何以臣为?”支期曰:“臣不
知也,王急召君。”长信侯曰:“吾内王于秦者宁以为秦邪?吾以为魏也。”支
期曰:“君无为魏计,君其自为计。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穷乎?安贵乎?君其
先自为计,后为魏计。”长信侯曰:“楼公将入矣,臣今从。”支期曰:“王急
召君,君不行,血溅君襟矣!”长信侯行,支期随其后。且见王,支期先入谓王
曰:“伪病者乎而见之,臣已恐之矣。”长信侯入见王,王曰:“病甚奈何!吾
始已诺于应侯矣,意虽道死,行乎。”长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于应侯,
愿王无忧。”
○华军之战
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孙臣谓魏王曰:“魏不
以败之上割,可谓善用不胜矣;而秦不以胜之上割,可谓不能用胜矣。今处期年
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玺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
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玺。夫欲玺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玺,其势必无魏矣。且夫奸臣
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仅仅。今王之地有尽,
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魏王曰:“善。虽然,吾已许秦矣,不可以革
也。”对曰:“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枭邪!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君劫于群臣
而许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枭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齐欲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
齐欲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曰:“齐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宝
璧二我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诺。”入说齐王曰:“楚,
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伐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
弗取也。”齐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
魏之璧马也。”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璧、马,有诸?”曰:“有之。”
“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
何益?若诚不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
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秦将伐魏
秦将伐魏。魏王闻之,夜见孟尝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为寡人谋,奈
何?”孟尝君曰:“有诸侯之救则国可存也。”王曰:“寡人愿子之行也。”重
为之约车百乘。孟尝君之赵,谓赵王曰:“文愿借兵以救魏。”赵王曰:“寡人
不能。”孟尝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闻乎?”孟尝君
曰:“夫赵之兵非能强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赵也。然而赵之地不岁危而民
不岁死,而魏之地岁危,而民岁死者,何也?以其西为赵蔽也。今赵不救魏,魏
歃盟于秦,是赵与强秦为界也,地亦且岁危民亦且岁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
也。”赵王许诺,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
又北见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约两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愿大王之救之。”
燕王曰:“吾岁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数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
行数千里而救入者,此国之利也。今魏王出国门而望见军,虽欲行数千里而助人
可得乎?”燕王尚未许也。田文曰:“臣效便计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计,文请行
矣,恐天下之将有大变也。”王曰:“大变可得闻乎?”曰:“秦攻魏,未能克
之也,而台已燔,游已夺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节割地,以国之半与秦,秦必
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韩、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赵之众,以四国攻燕,
王且何利?利行数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门而望见军乎?则道里近而输又易矣,
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听子。”乃为之起兵八万,车二百乘,以从
田文。
魏王大说,曰:“君得燕、赵之兵甚众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请讲于魏。
因归燕、赵之兵而封田文。
○魏将与秦攻韩
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
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
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
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其亲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雠之敌国也。
“今大王与秦伐韩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识也,则不明矣。群臣知之
而莫以此谏,则不忠矣。今夫韩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乱,外安能支强秦、
魏之兵,王以为不破乎?韩亡,秦尽有郑地,与大梁邻,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
地,而今负强秦之祸也,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
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之上党而攻强赵,则是复阏与之事也,秦
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之水,而以与赵兵决胜于邯郸之郊,
是受智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
甚远而所攻者甚难,秦又弗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与楚
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韩亡之后,
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矣。
“秦故有怀、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临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
矣。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过矣,乃恶
安陵氏与秦,秦之欲许之久矣。然而秦之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邻,听使者之
恶也,随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则南国必危矣。南国虽无危,
则魏国岂得安哉?且夫憎韩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
“异日者,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余河山以兰之,有周、韩而
间之。从林军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国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
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乎阚,所亡乎秦者,
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百,名都数十。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大梁也尚千里,
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而有郑地,无河山以兰之,无周、韩以间之,去大
梁百里,祸必百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韩不可得而约也。今韩受兵三年矣,秦
挠之以讲,韩知亡犹弗听,投质遇赵而请为天下雁行顿刃。以臣之观之,则楚、
赵必与之攻矣。此何也?则皆知秦之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
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乎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魏之质,以存韩为务,
因求故地于韩,韩必效之。如此则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然
而无与强秦邻之祸。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
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
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大破,卫、齐甚畏,
天下之西乡而驰秦,入朝为臣之日不久。”
○叶阳君约魏
叶阳君约魏,魏王将封其子,谓魏王曰:“王尝身济漳,朝邯郸,抱葛薜、
阴成以为赵养邑,而赵无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问阳、姑衣乎?臣为王不取也。”
魏王乃止。
○秦使赵攻魏
秦使赵攻魏,魏谓赵王曰:“攻魏者,亡赵之始也。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
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
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今国莫强于赵,而并齐、
秦,王贤而有声者相之,所以为腹心之疾者,赵也。魏者,赵之虢也;赵者,魏
之虞也。听秦而攻魏者,虞之为也。愿王之熟计之也。”
○魏太子在楚
魏太子在楚。谓楼子于鄢陵曰:“公必且待齐、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齐、
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恶于国者,无公矣。其人皆欲合齐、秦外楚以轻公,
公必谓齐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实首伐之也,楚恶魏之事王也,故劝秦攻魏。’
齐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听秦而为和。以张子之强,有秦、
韩之重,齐王恶之,而魏王不敢据也。今以齐、秦之重,外楚以轻公,臣为公患
之。钧之出地以为和于秦也,岂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还兵,魏王必惧,公因
寄汾北以予秦而为和,合亲以孤齐。秦、楚重公,公必为相矣。臣意秦王与樗里
疾之欲之也,臣请为公说之。”
乃请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轻秦。且
有皮氏,于以攻韩、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无所用之。”对曰:
“臣愿以鄙心意公,公无以为罪。有皮氏,国之大利也。而以与魏,公终自以为
不能守也,故以与魏。今公之力有余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
曰:“魏王之所恃者,齐、楚也;所用者,楼<广鼻>、翟强也。今齐王谓魏王曰:
‘欲讲攻于齐,王兵之辞也。’是弗救矣。楚王怒于魏之不用楼子,而使翟强为
和也,怨颜已绝之矣。魏王之惧也见亡。翟强欲合齐、秦外楚,以轻楼<广鼻>;
楼<广鼻>欲合秦、楚外齐,以轻翟强。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谓楼子也:‘子能
以汾北与我乎?请合于楚外齐,以重共也,此吾事也。’楼子与楚王必疾矣。又
谓翟子:‘子能以汾北与我乎?必为合于齐外于楚,以重公也。’翟强与齐王必
疾矣。是公外得齐、楚以为用,内得楼<广鼻>、翟强以为佐,何故不能有地于河
东乎?”
战国策魏策的原文与译文
最佳答案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译文】
庞葱要陪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庞葱对魏王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庞葱说:“如果是两个人说呢”魏王说:“那我就要疑惑了。”庞葱又说:“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了。”庞葱说:“街市上不会有老虎那是很清楚的,但是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像真有老虎了。如今邯郸离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多,而毁谤我的人超过了三个。希望您能明察秋毫。”魏王说:“我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庞葱告辞而去,而毁谤他的话很快传到魏王那里。后来太子结束了人质的生活,庞葱果真不能再见魏王了。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战国策魏策古诗文网)战国策魏策》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敬请关注baike.100xue.net,您的关注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